窗外的槐树影儿,在壁上印出弯曲的痕迹,仿佛盘踞于荒凉土地上的虬枝老根。他辗转反侧,偏又毫无睡意,只觉黑暗沉沉压了下来,竟至连呼吸也越发窘迫了。于是他坐起来,捻亮煤油灯,微弱的火苗在四壁之间跳动,勉强撑开一小圈昏黄,却照不亮黑暗的角落。
白日里,他照例与众人谈笑,滔滔不绝,显出热闹非凡的样子来。然而人散了,他每每回到独居的小屋,便如卸下了一副假面具,只是默默坐在灯下,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长,扭曲着贴在墙上。此时若有脚步声经过门外,他心头便无端一紧,侧耳屏息,几欲起身开门看看。可脚步声终究渐渐远去,他的耳朵又空落落地听不到什么了。他随即点起一支烟,深吸一口,烟气却在他喉间盘旋,呛得他连连咳嗽起来,他倒仿佛借此笑了几声,又迅速按熄烟卷,仿佛要扑灭那渺茫的烟缕,亦或扑灭自己心头那一点火星子。
他有时也走出门去,在院中踱步,听着梆子声由远而近,又由近而远。更夫沉重的脚步踏过,他竟躲进槐树后面,直待那人影彻底消融在黑暗里。他深知,自己如此躲闪,无非是怕自己期待的眼神被他人窥见,反而又换来一番空茫罢了。他于是悄悄踱回屋里,门扉紧闭,却将耳朵贴在门板上,细细捕捉着外面任何一点微响——偶尔,远处隐约传来几声笑语,他心头便骤然一颤,竟至于将脸紧贴在冰凉的门板上,似乎想贴近那飘渺的暖意。然而终究什么也没有,他只好将脸移开,门板上只留下一小片模糊的印痕,如同被弃置的残影。
更深夜阑,他重新躺下,吹熄了灯火,世界复归于漆黑。他闭眼,却又分明看见檐下蜘蛛不知疲倦地结网,网丝在黑暗中泛着幽微的光亮。那网在风里飘摇,丝缕相连又脆弱得随时会断裂——蜘蛛却固执地爬上去,修补着,缠绕着,仿佛非织就一张大网不可,即使没有飞虫来投,也要织下去。
他翻个身,脸朝墙壁,却觉得墙壁也冷冰冰的。他于是自嘲般轻哼一声,自语道:“倒也无妨,横竖孤灯独坐,倒也清静自在。”但窗外孤寂的梆子声又敲响了,一声,两声,三声……节奏单调地刺破这寂静,像在数落着无边无际的虚空。
他终究还是起身,重新点亮了灯。灯花爆响了一下,他伸出手指,竟不自觉地想掐灭那跳动的光焰。灯影之下,他脸上却浮出一点笑意,不知是对着灯火,还是对着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,终于再次吹熄了灯火,躺倒下去——灯油熬干了,光焰熄灭;只窗外檐角下,那固执的蜘蛛犹在结网,仿佛在编织着它永无回应的空梦。
长夜漫漫,人如檐蛛,那徒劳的丝线,织着空无的等待。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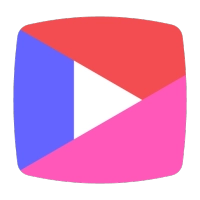


Comments NOTHING